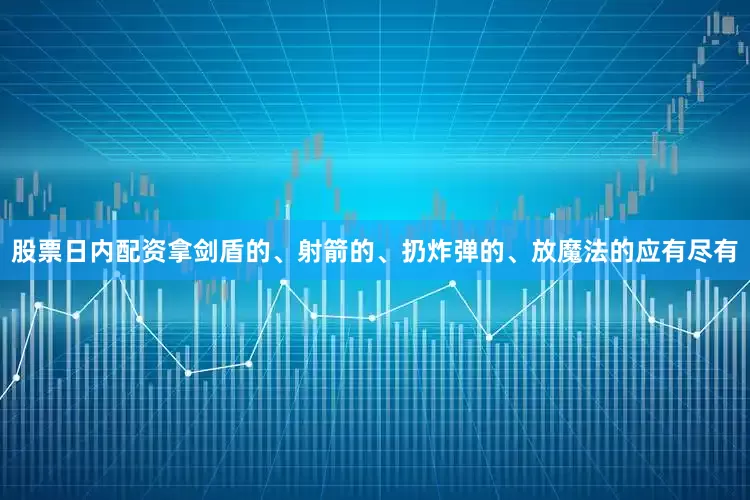听读者之声,与读者为友。为了更好地为读者服务,倾听读者的意见及建议,加强与读者的沟通与交流,当阳市图书馆专门开通了读者邮箱,希望广大读者把自己的人生感悟、意见及建议等写给我们,“读者之声”将定期择优刊登。
投稿方式:电子档文稿后面附上作者姓名、电话号码、个人50字以内简介、个人近照发送至:
知无不言,内容不限,欢迎您的来信。
第57期推出黎永松老师作品
黎永松,河溶镇卫生院检验科主管技师,当阳市作家协会会员。阅读和写作让我放慢急促的脚步,平静浮躁的心情,在放飞的日子有归宿,隔离的岁月不孤单。孤独的我读冷漠的书,我读故我思,我写我快乐,在喧嚣的世界里享受独处的欢娱,在苟且的生活中领悟诗意的人生。
上码头怀古
展开剩余85%甲辰浅冬,当阳市作家协会“为人民执笔,与时代同行”采风活动走进河溶。漫步古镇沿河街,从明末清初开始的遗迹,沉浸在时光中,整条街多为明清建筑,砖木结构,青砖黛瓦、风火墙、墀头,老宅幽深,天井重重。行至宋记早点老三样处,左拐进入沿河街二巷。
我们用脚步去丈量这段巷道,穿过由蔷薇搭建的圆形拱廊,到达上码头约百余步。巷左青砖黯淡,杂树葱茏,历数沧桑,人道是,青洪帮大哥曾住。尚有几户,耄耋老人,颐养天年,古色古香的老屋,犹如陈年老酒,在岁月中沉淀,越发醇厚,那雕饰的残破窗棂还彰显着昔日风华。巷右是河溶小学,始建于一九一四年,为川主宫所扩建。川主宫者,祭祀汉昭烈帝刘备,四川人的会馆,经营糖、盐、鸦片。扩建时起院墙围做校园,大门面向漳河,门前五步台阶,台阶下是大操场,而川主宫也成为学校的一部分,是老师的寝室和办公的地方。百年大计,教育为本,培养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建设者和接班人,一九九九年迁至溶新路新校区,这里也走下历史的舞台。如今那残破的院墙已推倒,建设义园广场,楚昭王粲,跨越时空,相会盛世,吟咏今昔,再次焕发青春。
伫立码头,极目远眺,漳水似弓,依偎古镇,上游蜿蜒,隐于两岸垂柳白杨之后,惹人暇思。想那漳河之源,挟裹天地之精气,孕育荆山之璞玉,始涓涓细流,变滔滔沮漳,演绎着卞和献玉的故事,诉说着金线拴葫芦的传奇。金线是那张家大堤,葫芦是那夹洲子,它包绕在沮河漳河之间。鸟瞰夹州子,并不是想象中的葫芦形,到像一个拱手作揖的谦逊老者,那民合村是戴冠的头,这里包谷芃芃,青纱帐深处有个神秘的卞家湖,他们的祖先是否为楚国献玉者之卞和,是否曾经从事玉石雕琢的行业,让人神往。那民耀村是略略前倾,拱手揖拜的身,这一揖,使夹州子平白无故的多出一块沃土,比较平直的堤岸线在这里显得婉延曲折,犬牙相错,漳水淼淼,首当其冲,洗刷不息,水灾频仍,人们在这修筑牛横庙,以镇那汪汪之水,到也安然。如今庙已不在,却矗有民耀酒厂,滴滴佳酿,润人心田。这一拜,使漳河在这里如钩似弓,水流湍急,漩涡翻滚,潆坑密布,造就了优良的港湾码头,古镇的"沿河五码头"均在这里,而上码头处于漳水似弓的中间,称为"弣"处,乃形势最险,河段最优,保存最完好的古码头。
拾阶而下,左侧开阔宽敞,与堤岸相隔一四方棱整的条石,雨余泛色霭霭,顺遂码头倾斜,平滑如镜,旁边字迹隽永清晰,"家國奠安厥功稱后",尽显小雅风流,名不虚传;右侧青石层层叠叠,犹如龙椅扶手,遮挡着上游侵蚀的土丘,墙缝中杂树横生,维叶莫莫,藤蔓攀附,维叶萋萋,笑摇清风,逗弄着穿梭其间的蛱蝶,娇美的触须在石棱上搔挠着,磷磷青石却不言苟笑,沐浴着残阳,默默数着曾经的日子,把它封闭在坚韧的岁月里。石阶渐渐,维其高矣,共廿四级,轮廓分明;厚实凝重,维其古矣,漳水润泽,色之凿凿;略为两层,平分秋色,痕迹显著,各占十二;每层开启之阶,巨石居中宽阔,琢为凹槽,犹如石椅,巧夺天工;下至阶底,遍植碳木,以护土石,百年浸蚀,略显腐朽,今更树石桩,环卫周围。
漳河依依,石阶谧谧,忆往日,曾经水波浩淼,啃啮码头,在这里书写丰富多彩的古镇传奇,上演活灵活现的小城故事。在那码头的绿杨荫里,有行色匆匆的启航人,是抱着革命理想的聂豫,带着民族气节的赵春珊;有才爬上码头的来客,是传播革命火种的傅子和,怀着共产主义信仰的董必武;有杀人不眨眼的日本兵;有鬼鬼祟祟的国民党川军;有无恶不作的土匪;有诙谐打趣的徐家三爹;还有吆喝着号子的船工,忙碌的挑夫,逐利的商人……。
清晨,河面上雨雾朦胧,隐隐约约商船如织,桅杆如林,码头开始繁忙起来。人们来挑水吃,从街巷的青石板走过,那木桶里的水"滴答滴答"不停,在青石上漫延开去,润泽如黛,更显光亮,就有人说,沿河街上的青石板非要漳水的滋润,才有灵性。船工挑夫也忙碌起来,上下货物,熙熙攘攘,吆喝声不断,那挑着缫丝的人群也加入其中。溶丝扬名海外,分为三等,上等丝不仅蚕茧质量好,制作工艺要求高,据说必须取上码头的水缫之。我想,那漳水挟玉石精气,在这段蜿蜒河道,千转百回,穿梭潆坑,而古码头处最曲,潆坑最深,洄溯幽寒,上天入地,水具灵性,取之煮汤缫丝,必为上等。
在这众生相中,有一人特别引人注目,高两米余,头大如瓮,五官和善,像如来佛,人称吴大汉子。祖籍四川,随父母来溶,早成孤儿,吃用面盆,孔武有力,以炕发糕做粩糟为生,常下河担水,踏过青石,湿脚印硕大,引来小孩嬉戏,用手比划,无限惊奇。不久日本侵占河溶,抓他到码头做苦力,一次他本已扛起一包盐巴,日本兵乘其不备又往他背上猛地甩上一包,致其腰闪断仆倒在石阶上,看着他痛苦呻吟的样子,日本兵发出狰狞的冷笑。从此吴大汉子驼了背,只和普通人一般高,他终身未娶,常悠闲憨坐在码头石阶上,小孩就围上去揪他又阔又厚的嘴唇,他也以逗小孩为乐,三年自然灾害期间,由于食量大,吴大汉子病殁于河溶福利院,享年四十八岁。在老一辈的童年记忆里,街上常传来吴大汉子的叫卖声,声音浑厚宏亮,尤其是冬日夜间,他提着用火盆烤着的枯发糕,佝偻着背,摇摆着像鸭子一样在街上边走边叫卖:“洋糖枯发糕哦”!"洋糖枯发糕哦"!几条街都可听到,那声音也在码头上空回旋,惊动了树上的乌鸦,啼叫着向远处飞去。
古码头啊!你是繁华的见证,古镇曾有一段如丝般的温柔岁月,那一艘艘载丝的船在古码头启航,撒下大把的铜钱,"咕咚咕咚"入水,祈祷一帆风顺。江西丝商熊杰夫来到河溶,采用较为先进的加工技术生产成品丝,冠以“金幅”商标试销上海,一举成名,后把溶丝扬名海外,在民国七年,引来外商外资渗入沮漳流域,首站便是河溶,美国“美孚公司慎大洋行”、英国“亚细亚煤油公司”、“巨丰烟公司”,还有私人开设的专营洋货的“松大烟公司”,在古码头先后抢滩于河溶,那洋轮游弋码头,可谓一时韶华,鹤立鸡群。也许亢龙有悔,物极必反,日本的侵略,匪患的连绵,河溶开始衰落。百年来由晚清的腐败颓废,灯红酒绿,鸦片殖民中,人们开始觉醒,变川主宫的鸦片经营为百年教育,化腐朽为神奇,成为立德修身,振兴家国的前沿阵地。同事郭君曾在这里有段难忘的求学生涯,常讲述在夏日漫长的午后,就有同学在睡午觉时偷偷溜到码头游泳,坐在两侧的倾斜条石上,象滑滑梯一样溜到水里,潜水下去一摸,就是几块铜板。游得累了,爬上码头,返回教室,在同学面前显摆所摸的孔方兄,辨认是康熙还是乾隆,殊不知,每块铜板背后都有一段精彩的启航故事。如今新时代,漳河生态修复,古码头俨然是重点文物保护单元,在那诉说曾经的传奇。
古码头啊!你是孤独的守侯,子然一生,饱经磨难的吴大汉子,常呆坐在码头,望着那日复一日的夕阳,永不回头的东逝水。码头成也漳水,败也漳水,漳河水库的修建和张家大堤的改道,古镇也脱离了频仍的水患,裸露的青石缺少漳水的润泽,显得灰暗,只有石阶间野蛮生长的草使它略呈生机,与天边如血残阳,共同描绘那壮美沧桑的画卷。守候着,守候着一年难得的几次大雨山洪,才能拥抱上涨的漳水,偶尔几个归来的游子屹立码头,怀念求学的青葱岁月,感叹易逝的青春年华。古码头在孤独中升华,在寂寞中沉淀,沉默是金,无声无息中显得巍巍。
古码头啊!你是人生的起点,有多少文人志士从这里出发,为民族带来了希望。你是生命的归宿,国民党川军偷偷爬上码头,躲在川主宫的八角楼里,酝酿一场阴谋,想把革命的火种扼杀在摇篮,是那傅子和以己之躯掩护同志们离开,热血洒在不远处的铁龙桥。"唯有牺牲多壮志,敢教日月换新天",在生与死的轮回中,起点与归宿同样精彩,书写绚烂多姿的古镇华章,探寻慨当以慷的人生意义。
编辑:卢思维
审核:谢晶晶
终审:徐海燕
地址:当阳市环城东路32号
发布于:北京市在线配资公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